被遮蔽的存在 关于王广义乌菲齐美术馆个展的访谈
艺术家王广义个展“被遮蔽的存在”于9月7日在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皮蒂宫正式开幕,此次展览展出艺术家创作的四个系列共28幅作品,其中部分画作是初次于欧洲展出。展览结束之后,艺术家的自画像将收入美术馆的收藏中。

策展人、馆长艾克-施密特(Eike Schmidt)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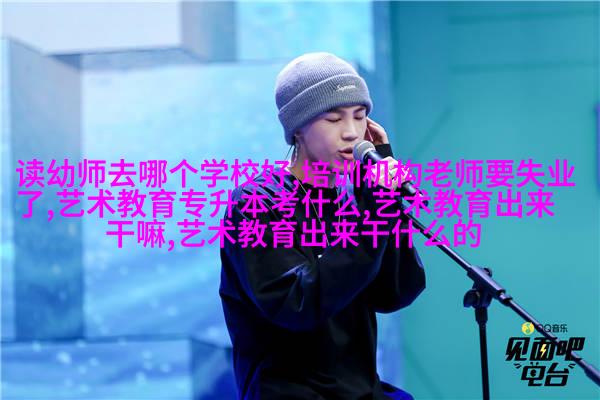
策展人德沐(Demetrio Paparoni)讲话
静谧安宁的家庭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与之亲密关联的空间背后,隐藏着什么?日常行为的重复性能否被解释为一种准宗教仪式?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疑问在“被遮蔽的存在”这一展览中呈现出来。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10日。
针对此次个展,意大利著名学者Elio Cappuccio与艺术家王广义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持续交流。现经艺术家授权首发于99艺术。
Elio Cappuccio:我想通过谈论将来在乌菲齐美术馆皮蒂宫展出的画作来开始这次访谈。这是你第一次在乌菲齐美术馆展出这些作品。你在中国和在欧洲办展览时,会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和想

乌菲齐美术馆皮蒂宫外景
王广义:在中国做展览时,它的文化和艺术的语境对于艺术家和观看者有一种默认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又会淡化掉作品中某种不确定的思想价值。而在西方做展览,由于观看者与艺术家的文化和艺术语境的差异,可能会让作品在差异的观看中让另外一种文化因素介入其中。比如说,波依斯的《椅子上的黄油》这件作品在西方展览时,它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取向,观看者有一种默认的判断;而当这件作品在中国展览时,中国的观看者可能会引入中国文化中“禅宗”开悟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作品,这种解读的方式无疑为波依斯的这件作品加入了另一个思想的维度。同样,我的这些作品在西方展览时也会面临这种状况。从这种角度说,所谓东西方文化交流,本质上是在“误读”的基础之上,让艺术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更加弥漫。

艺术家王广义讲话,左为意大利翻译Giulia Pra Floriani
Elio:同一件作品产生不同的解释与作品所处的不同语境有关。按照解释学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感知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的意义視域以及文化遗产而形成的。丹托在他的《眼睛的历史性》一文中写道,我们把符号附在某一个事物上,并不是简单地跟“看见”这个动词有关系,而主要跟我们脑子里在较长的时间内所继承的文化建构有关系。仿佛在说,眼睛的解剖结构历史上基本上没变,反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到历史转变的影响非常深刻。
王: 确实如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看见”的同一符号或者物体有着不同的感受,进而产生复杂的思想意识。无论是艺术家“看见”之后的创作行为,还是观看者“看见”之后的解读,其背后的原因都是由文化的历史性作为支撑。

Daily Life No.1, 2014, 180x14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乌菲齐美术馆的展览展出了《日常生活》系列(2013-2014)中的四幅画。在这些作品中,你描绘了私人的、甚至私密的事情以及物品,比如人在卫生间的时刻。在这些作品中,你选择的主题是人们独自面对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人们遇见其他人。
王:这几件作品是我在人到中年这个阶段,对于个体生命在权力结构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如果说我们都是在权力的“裂缝”中思想,那么个体生命的行为似乎也只有在私密的空间才能让“赤裸的生命”有一场自由的节日;而其人作为观看者而言,这场在绘画作品中表现的自由的节日彼此都是感同身受的。因为这个“赤裸的生命”无论生活在任何国度里,所面临的困境都是相似的。
Elio:你在画中表现“赤裸的生命”,就是通过表达我们人们生命的自然方面。这个问题是否与权力结构影响人际关系的方式有关?
王: 当然,在社会结构中是不可能能存在纯粹的自然人的。所有人都逃离不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所编辑的网络系统。当然,各个国家由于其以及社会的差异,进而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Obscured Existence – The Girl Taking Rest, 2018, 200x40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调查生物学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最多的哲学家是福柯。他的著作包括对诊所、监狱以及社会结构的研究。我有一个双重的问题想问你:你认为是否可以用福柯的哲学思考来解读你的创作?另外,福柯的哲学思考是否可以用来解读你这些最新的绘画作品系列?
王: 当然,某种程度上福柯的思想对于我有影响。特别是《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规训与惩罚》中解释,在现代社会中,权力试图控制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控制甚至会延伸到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指的就是生物,这也就是我理解驯化的意思。作为艺术家我的知识或者思想的来源非常混乱和复杂……我有时觉得艺术家的状态有点像一个没有“目的论”的“造物者”。这一点有些像哲学家德里达所说的“写作先于思想”的状态。
我近几年创作的“被遮蔽的存在”这一系列作品,是色彩在画布自上而下的流淌过程中慢慢地产生了思想。而引发思想的源头确实是我年青时代对于我的家乡哈尔滨(中国北方原始宗教的发源地)萨满教的场景记忆,色彩布条组成的幕布在后面的萨满“通灵者”与前面的观看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遮蔽的存在。再回到福柯,虽然这位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和我家乡的的萨满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并且控制的手段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注意到,这种控制在传统社会中也同样存在。然而,萨满教中,观众会产生一种被纳入到一个仪式中的感觉。观众不会感觉到他是被操纵的对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操纵。

Obscured Existence – Pietà, 2022, 140x18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考虑到我们的全球信息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差异,你作为艺术家怎么看这两种操纵模式之间的区别?
王:当然我知道艺术家创作时的原始想法与艺术家作品被解读时它们的思想脉络可能是不同的。
Elio:你提到了萨满教。在欧洲艺术中,最接近萨满教习俗的艺术家是波依斯,尤其是他对死亡以及与自然的关系的想法。你在乌菲齐美术馆展出的作品与波依斯的思想有关系吗?
王:波依斯是想让萨满这一原始宗教与西方的神学、思想通过艺术形成一条关于自然与死亡的思想的链条。但对于我而言,萨满的“去教义”化的难以捉摸的状态,让我以所谓“萨满的目光”的知识来重新发现那些经常被遮蔽的“自然物”以及被复杂“教义”的宗教埋没的故事图像。尤其是近些年呈现“人文传统”与日常生活的某些场景的作品就是通过这么一个过程创造的。当我以萨满的目光凝视这些场景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场景的一种仪式感。
从个人感受而言,这种“凝视”让我对那些以某种方式隐去的“物体”充满兴趣。而大家都认同,就像福柯说的那样,这种准宗教的“凝视”被权力以及权力对图像和文字的全部控制抑制了。我作为艺术家,其实是在萨满状态下的“凝视”和被遮蔽所带来的“视觉恐惧”之间去感受这种重叠的困境。

展览现场
Elio: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重点谈谈你创作《日常生活》使用的绘画技巧。你用照片吗?你是否在照片上画了一个网格,然后把它在画布上放大?还是直接把照片用投影仪投射出来了?简而言之,我想了解你创造这些作品的过程。
王:当我使用照片进行创作的时候,一般是通过打格放大的方法,将图像放大到画布上,然后随着一步步深入描画。这种网格的理性结构,在被使用的时候,我会用一种“自我授权”的自由观念来改变原来的图像,网格中的形象边界的被改变都是束缚与自由相互抗争的产物。这个过程中我往往会做一些变形处理。我从来不使用投影仪,投影仪投射的准确度太高了,反而会限制我的想象力。
在画面不断被一层层色彩覆盖时,其形状常常会出现不可控的偶然性改变。决定色彩的浓密与否是与网格结构所形成的物体边缘的清晰度相关联。我用流淌的色彩对画面进行“去图像化”的处理。将偶然性固定下来,对我是很重要的。

展览现场
Elio:在乌菲齐展出的作品中,你关注身体的日常平凡。虽然有一定的变化,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的关注在你早期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比如1987年的《黑色理性——白色卫生间》或《新宗教》系列中的部分作品。在《新宗教》系列当中,《哀悼》这幅作品中,图像来源让人想到米兰布雷拉美术馆的曼特尼亚名画;也就是说你的作品参考西方的绘画传统。佛罗伦萨的展览也包括这幅绘画作品的一个新的版本。另外展览还包括2018年《被遮蔽的存在》系列中的《病床》。这幅画参考小汉斯·霍尔拜因画的《墓中的尸体》。也就是说,在你的作品中,你再现在欧洲艺术中被广泛描绘出生去世的各个时刻。绘画中,身体的神圣化显然跟教有关系。这种神圣化,以世俗化神学的意识形态形式,也能够在很多作品中发现。在你的艺术研究中,为什么在历史、时代和宗教文化方面如此不同的人物都会出现?他们有哪些共同的特点?
王:乌菲齐美术馆展出的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偶像”,虽然支撑它们的文化动机各不相同。

Obscured Existence – Debater, 2020, 140x18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请问您怎么理解“偶像”化的存在这个概念?
王:我认为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许多次被的过程,而每一次的都会有一些“残留物”的存留,我把这种“残留物”称为“偶像”。无论这个“我们”生活在哪里,这些“偶像”就像“底片”一样随时都可能显影成像……各种仪式、偶像、遗物、戒律等是否在场,是我们所不能掌控的。我们只能靠“记忆的表象复制” 为这种“偶像”赋予一种历史的存在感。记忆的表象复制,我们并不能有意识地掌控它的在场与否,这种时而浮现、时而隐匿的偶像的底片是一种记忆表象在时间流逝的连续性过程之中不断被“复制”、被“持留”。当然,这种记忆的表象复制是需要被偶然性激活的。而人在孤立无援和迷茫无助的状态下,“偶像的底片”的不确定性和的历史视角的混合之下才能完成所谓的“表象复制”。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隐藏在事物的背后。

Obscured Existence – The Man Taking Rest, 2018, 140x18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你描叙的这种“残留物”是知识、记忆、事件等在我们头脑中留下的痕迹。这些痕迹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积累,并可能在不可预测的瞬间里面突然被激活。漂浮在无意识中的“残留物”图像是通过你说的“偶像”以及“底片”获得一个具体的形象。这让我想起弗洛伊德的多种驱动,同时也让我想起荣格的原型。这也类似于这有点像普鲁斯特分析的非自愿记忆以及“心灵的间歇”(intermittences du coeur);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已经被记忆删除的事件突然之间重新闯入我们的生活中。
王:“心灵的间歇”这个说法太好了,艺术家的创作行为,往往是在这个“心灵的间歇”的空隙处从集体无意识扩散的噪音之中与“此在的生活”感受产生某种重合。这种重合让创作者的和观看者在困扰之中仿佛感受到意识形态控制者的身影与声音的存在,进而质疑和穿透这一形成社会权力结构的想象性系统。

Fallen Angels, 2023, 270(H)X280(W)cm _ acrylic on canvas, arylic on canvas
Elio:你刚刚解释你与自然现象的关系。请问您怎么理解您跟东西方的历史以及图像传统的关系?
王:我们虽然能够观看人类已有的文明,不过都是隔了一层的。这一层是一种界限,同时也是一种关联。从小时候开始,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偶然的。就像我刚刚关于“偶像”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像“底片”一样在我们心中存在,等到在某一时刻它们又被“偶然性”激活,就会浮现出来。我们今天人的生活,都受到“底片”的影响。而“底片”所承载的时间和记忆的厚度,又会影响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在西方传统中,例如普鲁斯特在《寻找失去的时间》谈到 非自愿记忆。正如普鲁斯特所写的那样,被岁月掩埋的记忆会突然地闯入我们的生活中。再比如说我们梦中看到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形象。或者再说荣格的原型;所谓的原型拥有一种普遍性的、从来不变的价值,同时也在我们个人的心中发挥作用。

Obscured Existence – Paradise Lost, 2019, 180x14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您提到了荣格。在研究集体无意识问题时,荣格远远超出西方的传统。
王:虽然我读到荣格,但我其实并没有认真地了解荣格的思想,我知道中国的“易经”和老子曾深深地影响了荣格。作为艺术家的我感觉到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有一条相对稳定的线索可供学者进行讨论,但是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某种意义上是逃离这个线索的“特例性”的存在。就像我这几年创作的“被遮蔽的存在”系列作品,它们是否涉及到“有”和“无”的关系?作为艺术家的我对待画面中的现实人物和历史图像中的人物有如对待自然的态度,似乎不以一般所看重的“因果程序”为然。最大的困惑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与途径来引导人们去获得不可或缺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体验。
Elio:选择远离因果程序的原则,使你更接近于整体观/整体论;你采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自然现象以及不同的文化表现。这种观念存在于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继承下来的新柏拉图传统中;整体观/整体论后来被17世纪的科学机制所掩盖,只是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中重新得到关注。在东方,整体观/整体论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自然为那些摒弃机械论的西方思想家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分析心理学,从心理学家荣格到希尔曼(James Hillman),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希尔曼在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影响之下重新提出 世界的灵魂(Anima mundi)的概念。哲学家普罗提诺一直到柏拉图学院都会使用世界的灵魂这个概念。这个观念把自然视为一个伟大的生物体,其中每个元素与整体和谐相连,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也是如此和谐相连的。您是否认为这些观念可能为你提到的集体无意识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王:当你读到克服线性的因果程序原则时,人们第一反应会想到整体观、整体论以及循环的视野,这种讨论可以延伸到柏拉图传统和东方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哲学家在讨论和打磨概念时会有一条稳定的学理线索作为支撑。而艺术家虽然在打磨感性时,大脑中也总是被某些观念和概念所折磨,艺术家努力想在各种观念的搏斗之中找到一个方向和道路,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想到“理性的感性显现”的可能路径。艺术家更像一个站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的顿悟者而用“自我授权”的方式“留下痕迹”的企图是支撑艺术家创作的核心力量。

Obscured Existence – Evanescent Holy Baby, 2018, 180x140cm , arylic on canvas
Elio:柏拉图不欣赏模仿自然的艺术,因为他认为模仿自然的艺术是复制的复制。这是因为我们周围的所有事物本来就是各个理念的一种反映。理念世界包括道德价值、数字、几何图形。只有那些接近于表现数字-理念的画家才能属于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城市。因为这个缘故,波兰美学家Wladyslaw Tatarkiewicz写道,假设柏拉图有机会看到抽象作品的话,他肯定会喜欢。你在画布上勾勒一个网格,然后重新画出一个原有的图像,是否一种给现实加秩序的方式呢?看画的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不过还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就像德沐在2013年的目录中写道,网格将内部和外部分开,是同时保证交流和关系的一个手段。
王:首先,我们要区分能看到网格的作品和网格被事物覆盖住的作品。能看到网格的作品,该网格表达的可能与福柯理论所描述的控制感相关;而网格看不到的作品,该网格也许是真实的潜在本质。我的网格有一个不确定的意图,犹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对被理解为世界的技术和形而上学结构的Gestell(座架)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它是现实的结构。

Obscured Existence – People On The Ground, 2018, 200x300cm, arylic on canvas
Elio:对现实本质的表现既与柏拉图有关,也与20世纪的几何抽象主义画家有关。像蒙德里安一样,他们将本质与几何联系起来。还有另一派艺术家,我想到的是像弗朗茨-马克这样的表现主义艺术家;他们认为艺术的目的是通过改变事物的形式来表达其本质。回到你的作品:在一些画作中,你再现你自己,独自在一个空房间里;在另一些画作中,你描绘一个空的房间,其中一个人都没有。在概念和哲学的层面上,你的这些不同的表现模式有什么区别?
王:“房间”这个场所,对艺术家而言,它既是一个呈现时间流变和产生思想的空间,同时又是逃离被“规训”的避难所,艺术家的创作活动都是在“房间”这个空间中的“在场”和“不在场”的不断切换中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