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艺术品市场前景新篇章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天镜,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太阳……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

卡拉瓦乔与托马斯在《多疑者的托马斯》中展现过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到的伤口中。圣经中说,在所有使徒中,只有他不相信真的复活。他画出了托马斯的心灵纠结,也画出了宽容。在看这个画面时,我们不由自主地跟随着托马斯的手一起进入到了身体之中去感受,从而得到某种心灵救赎。
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中的“托马斯”,折叠、挤压自己身体,将现实中的不可能完成动作变成可能。这次,“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力的亵渎。尽管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但卡拉瓦乔宗教画与梅普勒索普照片所传达的情感力量却一样强大,都能牢牢吸引观众眼球,因为它们抓住了艺术本质,与希基相同,它们具有超越道德说的温馨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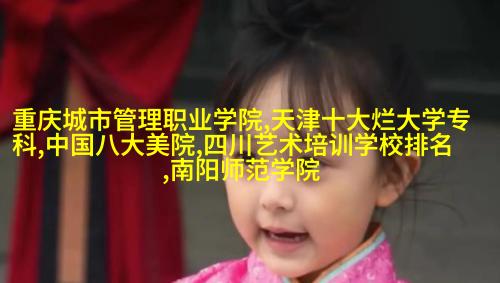
然而,由机构化博物馆文化、高冷学院主义教育和僵化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当代艺术系统否定了最吸引人的那一面,让枯燥乏味成为当代艺行最大问题。
90年代另一个提出“美”的辩护者是哲学家阿瑟·丹托。在1998年的论文《美与道德》里,他提出了美是一种触动内心方式,可以将悲痛转换为平静忧伤,将痛苦转换为温和愉悦。在文章中,他比较了林璎设计的大型纪念碑与克里斯·博顿设计的小纪念碑。他称赞林璎作品从概念到形式都不同凡响,而博顿作品毫无审美价值,只能提醒观众敌对方也有死者,却不能触动人心。

丹托认为20世纪之后,当一切皆可可能之后,不断理论化会使得"美"逐渐枯竭,把它简化成或人类学教材或商业宣传工具。而且警告那些追求纯粹感觉和享受的人,他们要警惕因为追求个体表达而忽略社会责任;他们必须扩展其视野,用更深层次哲学思想来阐释那些看似丑陋但其实蕴含深意的事物,比如杜尚的小便池等等。
丹托认同三类自然之美(如山川湖泊)、具有意义之 美(如精神内省)以及轻浮商业化之 美。但他批评后两类往往被误解或滥用以服务于权力结构,使得真正正义的声音无法被听到。他认为真诚探讨这些问题是关键,以避免陷入肤浅的情绪主义,并寻找如何让这些探讨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作用。

安尼什·卡普尔(Anish Kapoor) 是极少主义及观念性流派融合形式与内容的一位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如《怀孕》(When I am Pregnant, 1992),通过简单几何形状凸显出生命即将破土而出的状态,其光影效果模糊了物质现象与消失之间界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沉浸式体验,同时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如同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笔下的田园风光那样忠实记录着时间变化带来的不同的景象。此外,《天镜》(Sky Mirror, 2001)则反映周围环境,与每个展示地点产生独特互动,这件巨大的圆形镜子既像天空照耀,又像是反射世界的一部分,让我们再一次思考自身关系于自然环境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