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老修鞋匠逆袭成裸模数据显示艺术追求超越年龄界限
在重庆西南大学美术学院,67岁的老冯世福成为了模特,他的故事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尽管他的外表给人一种50多岁的印象,但他依旧保持着强健的体魄,这让他能够长时间地站立在教室里,为学生们提供模特服务。

老冯每天都穿梭于艺术与皮鞋之间。他是一名皮匠,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铺里补鞋子,收入平稳。然而,他也有另一种职业——当模特。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裸露身体,更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
讲台上站着一名全裸男子,丁字步、双手交叉自然下垂,眼睛望着地面或者斜下方某个想象中的物体。这位年迈的男性身体虽然线条模糊,但充满了时间留下的痕迹。不说破,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老冯在大学里担任12年的模特,一堂课穿衣100元,而裸身150元,比补皮鞋好,他本身就是一名皮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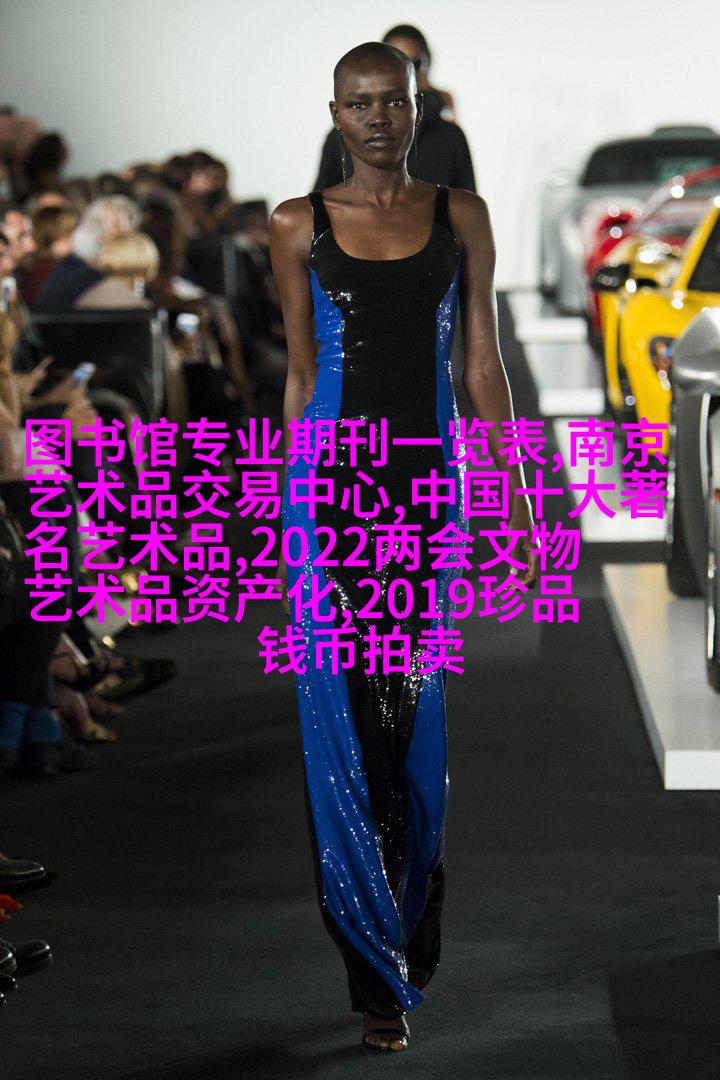
天光教室是一个特别设计的地方,有几块巨型玻璃,从顶部自然光照射下来,在模特身上反射和折射,为艺术创作提供无限角度和色彩。老冯站在玻璃侧下方,一节课40分钟内会根据老师要求调整姿势,有时候躺,有时候站。
付念屏教授忙碌地指导学生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一位女生比老冯孙女大不了几岁,她正在调颜料时看到了一眼,就又低头忙自己去了。她没有感到羞耻,没有害怕,因为这是艺术的一部分,是学习的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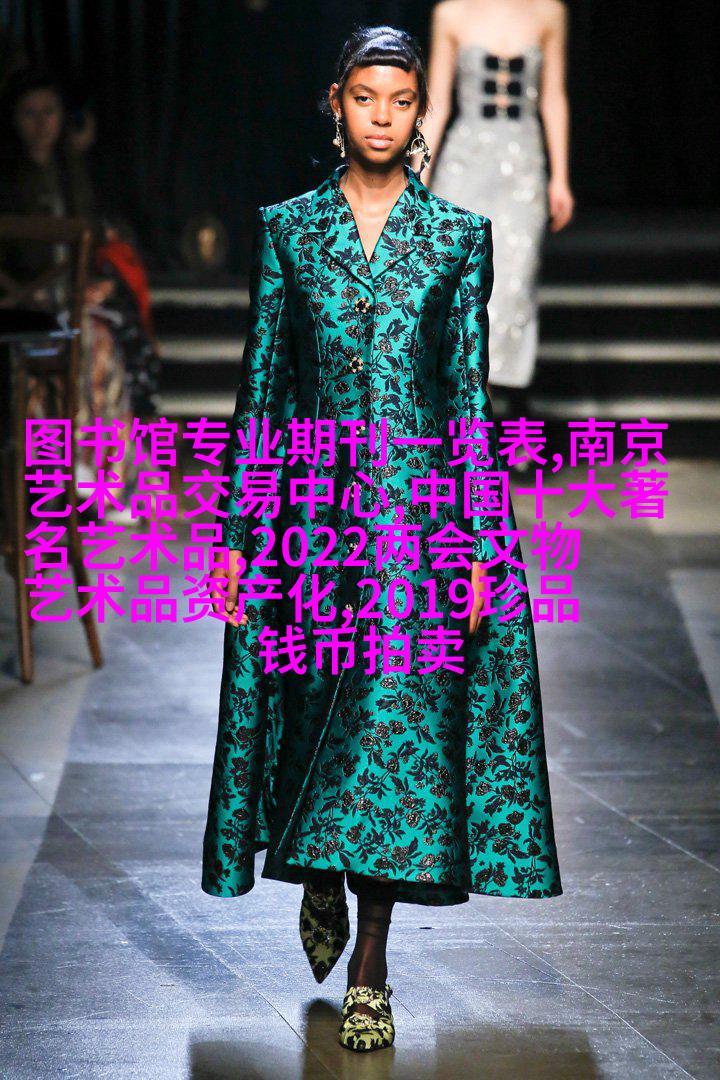
付念屏教授非常强调颜色的重要性,在老冯身边比划解释,“某个皮肤皱褶的阴影”,每个学生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到不同的颜色。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只是单调的人肉色,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是无尽丰富的灰、黄、绿以及它们混合后的颜色。
小学毕业后,老冯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当他听到这些关于数据驱动和数字化时代的事情时,他觉得有些吃力,但是他认真听着。他对这方面并不熟悉,但是他总是在努力学习新事物,不断提升自己。

11月中旬,当外面的温度只有11℃时,付念屏喊来两个取暖器对准讲台上的取暖,同时还专门为讲台上铺上了棉絮。此刻,小学毕业年龄段的人类身体展现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被重新定义为“美学”。
通常情况下,一名模特会静默40分钟,不喝水,不说话,只需保持姿势。但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由于气温较低,所以需要额外措施来保证安全。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最安静的声音也能造成微小震动,使得整个教室显得格外宁静而神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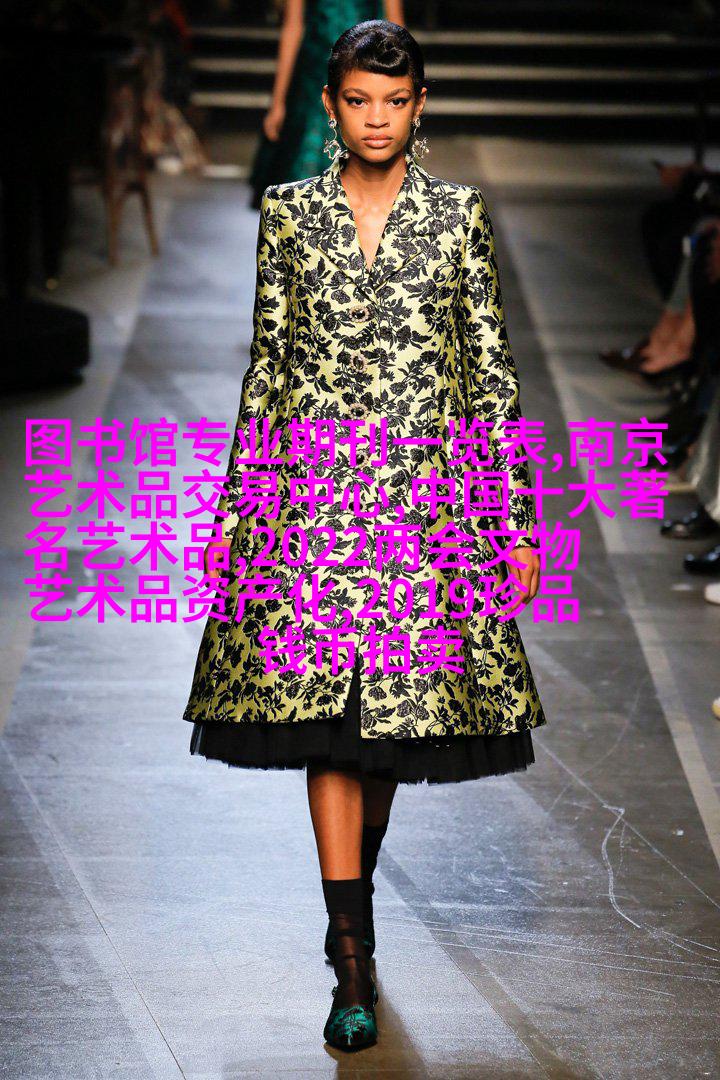
接近课程结束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一个女声唱得那么响亮,让整个教室微微震动。这次课结束后,当所有人准备离开时,其中一位同学把手机递给老师,说:“我在上课,我等会再打。” 老师点点头,然后继续进行教学活动,如同之前一样专业而严肃,无论周围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被打扰或分心去应对其他事情,只专注于教育任务本身这一点,是任何教师所追求且努力做到的标志之一,也正如我们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实践的一种理想状态:即使是在极其复杂多变的情境中,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最终实现个人与集体共同目标与愿景。
随后,我们跟随导师前往位于北碚城边上的那间古朴但充满活力的皮匠铺子,那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张,上面写满了来自不同年代不同情境的心灵感悟,以及关于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这些文字都是由过去和现在交织而成,它们既是一份回忆,也是一份希望;既是过去经历,也预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挑战。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以及如何通过学习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
走进这个小小工坊,你可以感觉到空气中的木质香味,那里的灯光柔软而温馨,每一个角落都透露出一种独有的温情感染力。你看得到那些工具箱、针线包、小凳子,还有一些废弃材料,这些都是用来修补日常用品的手工艺品制作所需的一切工具。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画架,上面挂着一些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中的作品,他们似乎在向你诉说故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作者的情感深处所隐藏的情绪。
随之进入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那里有一套精致简约的小沙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几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大量书籍。我知道这儿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这里不仅有知识,还有我一直渴望探索的问题答案。我紧握笔记本,对那些我尚未了解清楚的问题提出疑问,并请求他们帮我找寻答案。
随后,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应该考虑更多可能性。我决定将我的问题转述给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杨姐,她开了一家餐馆叫“琴琴早餐店”。她让我惊奇的是,她并不介意回答我的问题,而且她的回答让我明白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项。我告诉她,如果她能帮我解决问题,我会买两杯咖啡给我。她笑笑说:“不要这么麻烦。”
最后,当你走出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以及愿意倾听别人的声音。你不必急于找到答案,而应当享受旅程本身,因为它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那天晚上,当你回到你的房间,你将带回很多新的思想、新见解、新经验,以及一次难忘旅行。那就是当代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它展示出我们如何通过简单却深刻的话语,将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文/王诗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