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艺术品一级市场的抽象探索路径
广东本土艺术品一级市场的抽象探索路径:从前卫美术到当代艺术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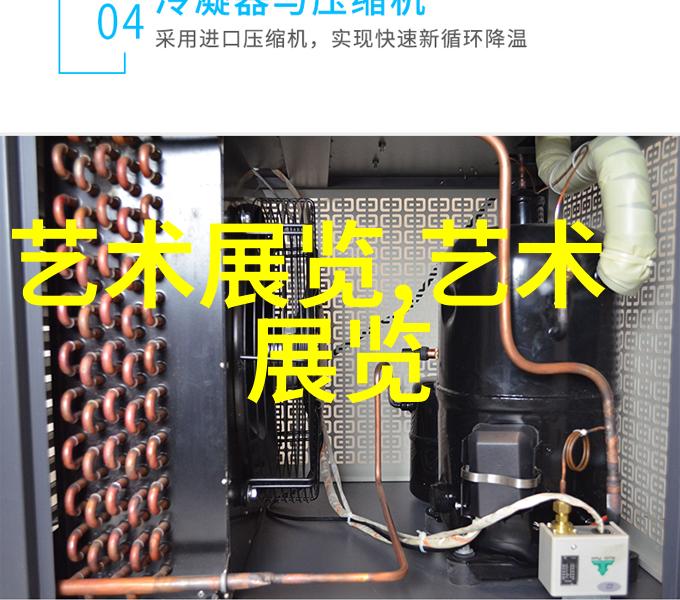
在中国近年来,抽象艺术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这样的潮流中,广东地区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热度。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
我们知道,所谓的“抽象”在中国本身就有着复杂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抽象型”这个词来对应那些区别于具象写实艺术的前卫探索,并将这种探索置于整个20世纪的长时段中进行审视。

20世纪30年代,以梁锡鸿、李东平、赵兽等广东籍艺术家为主体的前卫美术团体中华独立美术协会成立,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影响,并与日本形成了现代美术网络。在这里,“前卫美术”更多地指的是野兽派、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等,而1935年8月《艺风》第3卷第8期发表梁锡鸿关于塞尚、马蒂斯以及立体派形式问题的文章,以及1935年10月《艺风》第3卷第10期“超现实主义介绍”专号发表梁锡鸿对赵兽与毕加索、勃拉克、米罗等并称,以及1934年的王益论关于康定斯基论文,都构成了追溯广东抽象型艺术发展史的一些星点痕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实验几乎一度中断,但改革开放后,1981年起,在广州美术学院教学大楼105号房间形成了一批院内外勇于探索的小沙龙,以李正天为核心,他们不仅举办了油画展,还将这种探索落实在教学改革上。他们还开设了“抽象造型”基础训练和创作课,对具象写实一统天下的惯常教育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极大地开拓学生们视野和思维。

除了这些,更有一些先锋团队如南方艺术家沙龙在1986年至1987年的活动,以及之后出现的大尾象、“一代”,阳江组以及实验水墨运动等,当代艺术群体和现象,也都对广东省域范围内乃至全国性的文化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广东抽象类型作品并不一定形成特定的团体或流派,而是掺杂在以上部分团体之中,或以个人的方式选择了一种具体形式。而张晓凌、孟禄新分析道:“1986年后许多人转向抽象不是简单源于形式实验,而是因为只有抽相才能构成一种‘纯粹’姿态,只有形式游戏足以表达理想主义失望及荒诞感,只有‘另一个世界’中的艺术才可能开始重建。”

回顾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分出几种倾向:70年代末以来的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派结合;8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是西方表现主义语言;再就是近十年的强调观念修为的人类存在。这三类出现在不同时间阶段,不一定替换关系。但对于中国本土如何去理解这段历史,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