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荒诞戏谑背后的严肃问候
在艺术家王庆松的世界里,头上总是顶着一丛触电般炸开的白色发丝,这是他标志性的发型。这个发型是对已逝母亲的一种缅怀,他从未梦见过母亲,因为他觉得母亲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成功,是带着遗憾离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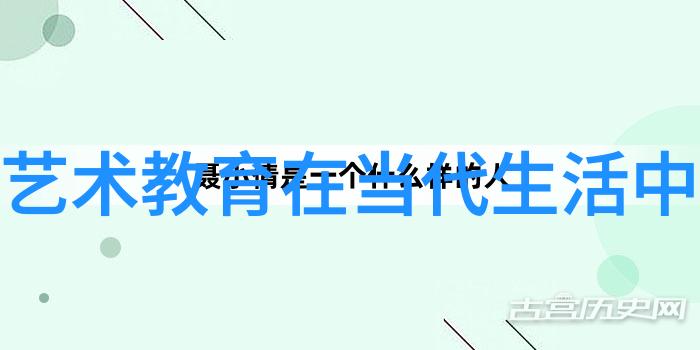
如今,王庆松已经成为被国内外美术馆收藏最多作品的中国摄影艺术家。他每年去祭拜母亲依然把画册烧给她看。这位中国最贵摄影师2008年的作品《跟我学》在伦敦佳士得以43万英镑(约合593万人民币)成交,创造了中国单幅摄影作品的最贵纪录。
《跟我学》,120x300厘米,2003年 © 王庆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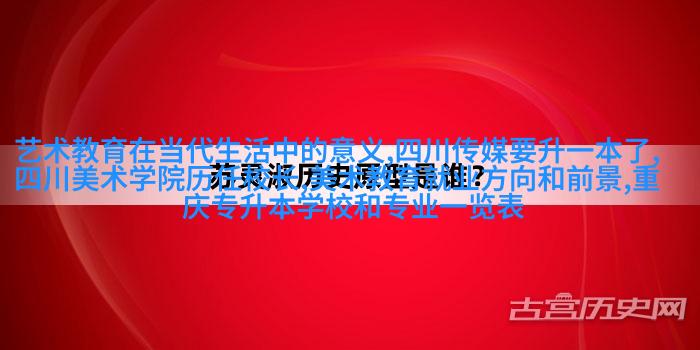
这幅照片拍摄于2003年,当时王庆松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搭了一个长8米、高4米的黑板,上面写满了中英文词汇和句子,有些甚至有明显错误。艺术家本人坐在画面正中,用教棒指向黑板。“学习英语令我压力很大,正是这种压力给了我灵感,让我拍出了《跟我学》。”王庆松坦言。
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里,从老百姓的视角来感受生活、发现问题,并带有一种老百姓特有的趣味。而且,纵观王庆松多年的创作,你会发现他会针对同一类问题回看过去,并结合当下的情形给出新的回答。

2013年的《跟你学》中,王庆松构建了一间教室场景,墙上写满了标语,全桌摆满书籍。疲惫的人们趴在桌上。荒诞的情境仿佛是中国教育现场的浓缩,也追问了社会中的教育问题。
他的成长历程波折重重,即使曾经作为油田子女,他还从事七八年的钻井队工作,但却与农民打成一片。他说:“大家经常拿东西来换画,我记得有个农民用一袋土豆和二十个鲜鸡蛋换了一整墙仙鹤。”

大学毕业后,他揣着1200块钱一个人跑到了北京,“谁也不认识,我住在圆明园画家村。”他带着一种“饥渴”,咬紧牙关一点点摸索。在1996年,当代艺术开始多元化的时候,他逐渐转为使用PS介入摄影创作。
1999年的《拿来千手观音系列之一》,用PS技术展现贪欲横流、虚伪浮夸社会。但20年后的《送往千手观音》,虽然构图相似,但内容已大变样:手里托起的是燕京啤酒到拉菲,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从胶卷到数码。这意味着不同时代人的消费观变化,即使是一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在站立于王慶 松 的作品前也能明白传递关于消费、中西方文化碰撞等等观念,不再困惑于当代艺术晦涩难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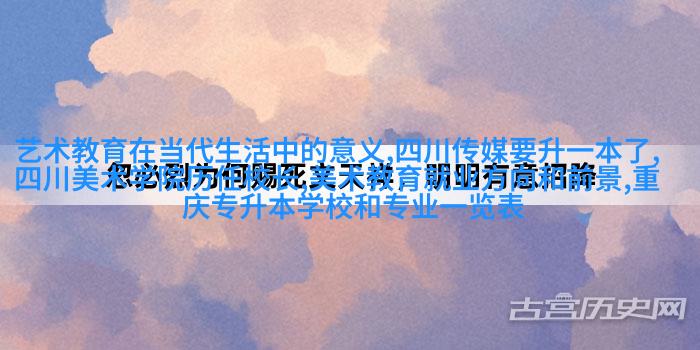
他的作品里充斥大量符号,有商业标识、各种鲜艳媚俗形象、大量农民工模特和粗糙画面感,这反讽语言典型。一位著名独立评论家评价他的作品:“只穿花条,以及白菜、垃圾桶底座亵渎滑稽象征意义……锁定这种崇拜所具有农民爆发气息。”
栗宪庭家的沙发睡过罗中立、方力钧……这些重要人物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一年,他赌上所有家当,“把妈妈去世前10个月工资,我老婆奖学金余下的钱,都押进去了”,第一次拍下大画幅《老栗夜宴图》,惊人的代表作,为代表人物奠定基础。
通过拍摄前一系列精心设计和布景,将不同的视觉经验融合,以展现人类生存状态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话题,从而引发更深层次思考。在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在国际融合还是个人梦想追求方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LOGO密密麻麻填满巨大的黑板,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站在审慎角度看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