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当代艺术收藏品市场转向新篇章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等。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卡拉瓦乔与梅普勒索普
戴夫·希基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他预言,在未来的十年,“美”将回归,在当代艺术中再次成为重要议题。在《不可见之龙》中,他向反美学倾向提出强烈。在他看来,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到现代主义大师,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和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创造都是一场纯粹探险。

比如,《多疑的托马斯》展现了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伤口中。圣经记载,这位使徒对复活持怀疑态度,而卡拉瓦乔画出了托马斯的心灵救赎。而梅普勒索普则以其摄影作品中的“托马斯”,折叠身体,以超乎想象的手法完成动作,将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事变为可能。这时,“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上,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的亵渎。
尽管意义和道德指向全然不同,但这两种作品传达的情感力量相同,都能牢牢吸引观众。因为它们抓住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即便意味着超越于道德说的感觉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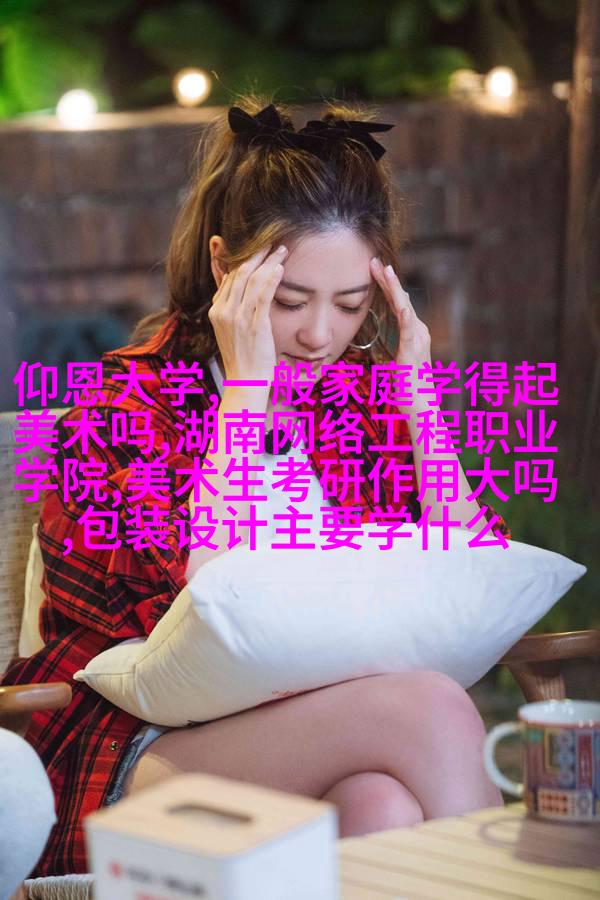
阿瑟·丹托
克里斯·博顿《另类越南纪念碑》

90年代另一位坚定地维护“美”的理论家是哲学家阿瑟·丹托。在1998年的论文《美与道德》(Beauty and Morality)中,他提出了关于如何通过悲痛达到平静忧伤,以及如何从痛苦获得温和愉悦。他比较了林璎设计的大型纪念碑,与克里斯·博顿的小型纪念碑,并认为林璎更接近真正的情感表达,而博顿却缺少这种深层次的情感触动。
丹托警告我们,不要让过度理论化导致对“美”的枯竭,使得所有内容都变得单调而缺乏激情。他认为必须重新考虑那些被遗忘但仍然令人享受和愉悦的事情,因为这些才是真正让人类感到快乐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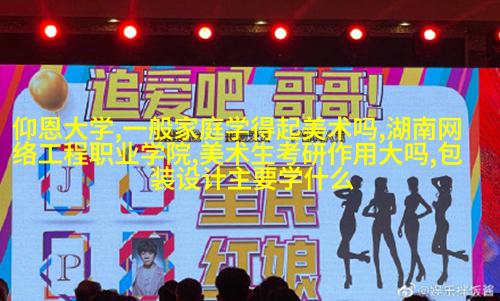
安尼什·卡普尔
90年代初,“ 美”似乎在当代艺术实践中有所回潮。英国印度裔雕塑家安尼什·卡 普尔(Anish Kapoor)的工作尤其值得注意,他试图融合极简主义与形式上的表现力。这件名为《天镜》的巨大的凸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既像是墙壁的一部分,也像是独立存在;既是具体形象,又是在空气中的虚幻体现。当光线照射到它上面,它就像是一个生命即将破土而出的状态,让人沉浸于宗教般冥想与世俗期盼之间。此外,其它地方展出时,它能够反映不同的环境,与观众产生不同的交流效果,无论是在自然景致还是城市环境下,都呈现出独特而深刻的情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