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亦杨美的回归古董收藏品交易中心中的当代艺术转向
自1960年代以来,理性的、观念性为主的艺术一直占据主导,冷漠、酷炫、丑陋甚至“恶心”成为当代艺术的研究热点,美和美学被抛到一边。然而,近20年来,当代艺术界出现了“美的回归 ”趋势,比如:卡普尔的大豆、大型光雕刻作品,如《天镜》、《多重反射》,埃利亚松的人造彩虹、太阳……艺术似乎在回归情感,转向一种热情的、亲密的、感性的艺术实践。

美的复兴还是美的滥用?
卡拉瓦乔与托马斯之间的情感纠葛

梅普勒索普与宗教救赎
戴夫·希基(Dave Hickey)是最早把审美问题拉回到当代艺术讨论中的批评家。在《不可见之龙》(The Invisible Dragon)中,他向当代艺术中的反美学倾向提出强烈。在他看来,从文艺复兴大师拉菲尔(Raphael)、卡拉瓦乔(Caravaggio)到当代艺术家梅普勒索普(Mapplethorpe), 无论作品是否带有功利目的或说教成份,艺术创造从来都是一场纯粹的、充满乐趣的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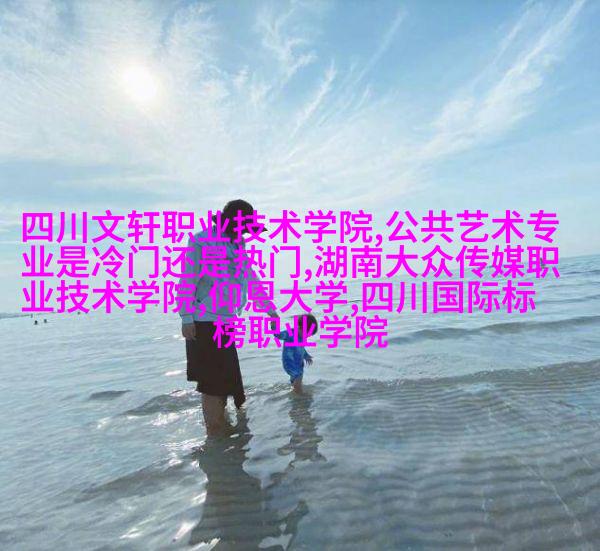
比如:卡拉瓦乔在《多疑的托马斯》中表现过一个特别感性的场面:托马斯把手插入到的伤口中。圣经中说,在所有使徒中,只有他不相信真的复活。卡拉瓦乔画出了托马斯的心灵深处,也画出了宽容。而在梅普勒索普摄影作品(包括SM内容)中,“托马斯”的质疑转到了人自身存在,有时甚至变成了对神的一种亵渎。尽管不再有宗教救赎,但图像本身仍能牢牢吸引观众,因为它们抓住了某种超越道德指涉力量传达出的温暖和触动。
然而,由机构化博物馆文化、高冷学院主义教育和僵化意识形态构成西方当代藝術系統否定了藝術最吸引人的部分,使枯燥成為當代藝術最大問題。

克里斯·博顿《另类越南纪念碑》的悖谬
阿瑟·丹托关于“美”的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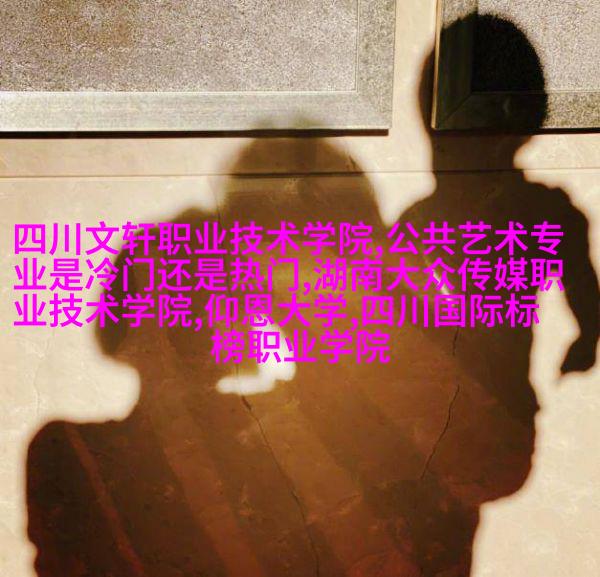
90年代另一位“美”的辩护者是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他提出了关于“激发心灵”、“悲痛转换为平静忧伤”,以及将痛苦转换为温柔愉悦的问题。在文章中,他比较了林璎(Maya Lin)与克里斯·博顿(Chris Burden)两人的作品,并警告20世纪之后一切皆可可能后,将理论化导致" 美"枯竭,让一切简化成人类学教科书。
丹托不同于希基,不认为" 美"是终极目的,而是在2003年的《百年演变》(The Abuse of Beauty)一书中追溯了" 美"概念过去100年的演变,并探讨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概念为何被抛弃,从而扩展了其领域,用更深层次哲思去解释那些看似不合适时尚标准但实际上蕴含深意的事物,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安迪沃霍尔肥皂箱,以及达米厄苍蝇等现象。这正体现出现代社会对于视觉语言和情感表达不断拓展的一种需求。
因此,无论如何定义,“错综繁杂”或简单地称之为“失去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审查标准下的束缚,而是走上了更加包容各式各样的表述方式及情感体验路径的手步。此过程并非简单地恢复往昔,而是在追求更多可能性同时也要应对挑战,即如何保持内在价值,同时融入外部世界,以此寻找新的视角、新形式、新意义——这正是我国古董收藏品交易中心所展示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既包含历史沉淀,又推陈出新,是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互动交流的地方,也许正是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意义上的新旧交融,为现代文化提供新的视角。